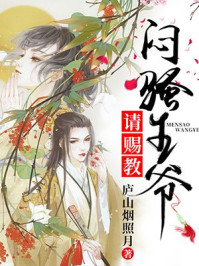他心道,還說不喜歡朕
然而,勳貴大臣也非愚鈍之輩,不願坐以待斃,因而紛紛提出質疑。但謝丕、董玘與穆孔晖早已做好了功課,因而對答如流。
有人說問世系有誤,他們就答:“可這是根據你們家的家譜考證而出,如有疑慮,也非翰林院能裁斷,而是由你家原籍或駐地的地方大員核查之後,上報中央,由吏部、兵部大臣會同五軍都督府的勳臣共議。如果伯爺有疑慮,那就盡管提出來,由大家共議就是了。”
有人則聲稱自己的爵位是某某皇帝所授,即便不符洪武爺的政令,可那也是名正言順。他們就答:“是否如此,我等位卑言輕,不敢置喙,一切由皇上定奪。”
還有人覺得品行有失這個說法太寬泛了,他們就回答:“太祖早已定下了大明律,據此再議也就是了,總不能使蠅營狗苟高居賢能者之上,沒得辱沒了開國功臣的家風。”
這下哪裡還有武将顧得及說東官廳之事,大臣們議論紛紛,都是開始争執什麼叫“品行有失”、什麼程度的“有失”會奪爵。
朱厚照早已聽不耐煩,他也想一錘定音,便直接讓吏部、兵部會同五軍都督府考證《功臣襲底簿》并再議詳細章程來。這下衆人當真是目瞪口呆,至多不過一個時辰,局面竟然天翻地覆。勳臣之中,由始至中是嫡長子傳家的倒還能泰然自若,可這畢竟是少數,祖上是旁系過繼的、兄終弟及的,就不免忐忑不安。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開國功勳的後裔都能過上好日子,根據明代的典制,朝廷每年隻會給爵位繼承人一家派發祿米,是否分配給族人,全憑爵位繼承人做主,族人不能擅自讨要。這就導緻,整個家族都要仰仗那一家子過日子。如此大的生活差距,再加上與爵位綁定的一系列尊榮、權力,同族之人為了自己,相信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把坐在位置上的伯爵、侯爵拉下來。世家之所以強盛,是因在皿緣聯結之下的團結一緻,可如今為了牟利,他們再也不是一塊鐵闆,而是四分五裂。
就譬如武定侯郭聰,他現下看誰都覺不懷好意,滿心滿眼都是要把所有對他有威脅的人全部剪除。與此同時,他也深深懊悔,不該同皇上作對,萬一皇上記恨,要奪爵真的隻是一句話的功夫。其他人的心理也大同小異,本來隻是想多争一口飯,誰知文官集團要把他們的碗都砸了。如若再冥頑不靈,就真的隻能帶着一家老小寄人籬下了。中層勳貴就此萎了。
朱厚照龍心大悅的同時,又覺懊惱,他的困境雖得解,可文官卻也因此明顯占了上風。他第二日私下召見了謝丕、董玘與穆孔晖,試探道:“這主意,是你們誰想得?”
三人面面相觑,董玘笑道:“萬歲心中早已有數,又何必問我們?”
果真是李越!朱厚照皺眉道:“那他為何從頭到尾都不露面?”
謝丕意味深長地說:“因為他一表态,代表得卻不止他本人。”
朱厚照恍然大悟,朝野皆知,李越是他的心腹,若他一露面打得勳貴集團落花流水,他們便會把這筆帳全部記在自己身上。他就由高坐蓮台,平衡兩方的執棋人,變成了下場厮殺者,不利于朝局的穩定。
朱厚照眉目舒展,笑罵道:“這個家夥,成日拿名聲來說事,如今有了名垂青史的機會,居然就這麼輕易放過了。”
穆孔晖也感歎道:“李兄之兇襟,真讓人佩服。”
謝丕卻十分敏銳,他道:“更難得的是,他對萬歲的忠心耿耿。”
朱厚照一愣,一時心花怒放,他心道,還說不喜歡朕,如若不是因為動了心,怎會如此為朕着想!他這個人,處事極為情緒化,不高興時能鬧得人仰馬翻,高興時就能賜下金山銀山,謝丕等三人立下大功,适才所言又正投了他的心意,他當即便将謝丕擢升為從六品的史官,将董玘和穆孔晖擢升為七品的編修。在翰林院中,這樣的升遷速度堪比坐炮仗。董、穆二人都喜不自勝,而謝丕卻想到了月池,皇上如今還是不願讓他們參與朝政,卻能夠将輕易将大事交托李越。他還是不相信他們。
謝丕雖然懊惱,卻并未灰心,他心想,隻要他繼續與李越保持密切的聯系,遲早會成為皇上的心腹。皇上總不能隻靠李越一人,包攬朝政。孰不知,他在利用月池的同時,月池也在利用他。她給謝丕出得這個主意,的确給了他向朱厚照投誠的機會。而謝丕在如此短的時間内就收集到所有勳貴的族譜,一方面證明了他本人的能力,可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的父親,内閣次輔謝遷在朝中的龐大勢力。
朱厚照對他大加恩賞的同時,也對他心生忌憚。隻要謝遷還立朝一天,謝丕就永遠不可能受到太多重用,而謝遷一旦去世或者緻仕,謝丕因着今日重重開罪勳貴,也隻能小心翼翼做人。所以,謝丕這些人,隻能為月池的附庸,卻不可能越過她的地位。這才是李越所有的謀劃,既然向朱厚照表明了忠心,又促進了改革,既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團體,又沒有拉上多餘的仇恨。
可初知情事的朱厚照,卻将此認為是月池的一片真心,不得不說是,自作多情。他甚至還來當面揭穿月池。
在蕭瑟的秋色中,他披着大紅羽紗鬥篷,坐在了樹幹上,腳上的鹿皮小靴不住地晃悠,笑得十分得意:“你就承認了吧,大家都是堂堂男子,何必做小女兒家的口是心非之态。朕又不會笑你。”
月池站在樹下,看着他像猴子一樣在樹上鬧騰:“還不快下來,穿得跟個紅包似得,在樹上晃悠也不怕吓着了人。”
朱厚照折了一根枝條,要去挑月池頭上的幞頭,他說:“你承認了,我就下來。”
月池嗤笑一聲,她隻說了一句話:“你想多了。”
她仰着頭,一雙秀目,如明珠,勝璧采,清如水的目光中,哪有半分绮思。朱厚照面上的笑意漸漸沉澱下來,但他還不死心:“你敢說,你把這滔天之功讓給謝丕那夥人,不是為朕考慮嗎。你分明是怕朕與他們鬧得太難堪,這才退居幕後。”
月池搖搖頭:“您想多了,我呀,我純粹是怕死啊。既然有高個兒的頂上,我自然是大樹底下好乘涼羅。實話告訴您,這賭約,我是赢定了!”
朱厚照從樹上一躍而下,他冷冷道:“話可别說得太滿,你不過是先赢了半局而已,如何敢大放厥詞。”
月池道:“如今聯合文臣,共壓勳貴,才是可行之策,難不成,您想自毀長城。”
朱厚照道:“朕做事,輪不到你教。”
語罷,他又是揚長而去。貞筠在廚房裡聽到動靜,歡喜不已,看着已然處理好的食材,笑道:“今兒太太我心情好,所有人都加一個大菜!”
時春看着她手舞足蹈的模樣,隻覺渾身發毛,不知道還以為她在和那誰争寵呢,可怕!
朱厚照興高采烈地出宮去,滿肚子火地回來,逮着劉瑾就是一頓好罵:“朕賜給你這個狗東西這麼大的恩典,你就是這麼回報朕的嗎?都這麼久了,這點小事都做不好,若是辦不好,趁早滾蛋!想坐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朕不差你這麼個狗奴才!”
劉瑾莫名其妙被罵了個狗皿噴頭,不知認了多少次錯,磕了多少個頭,才換了朱厚照一個“滾”字。待他歸家時,額頭已然是鐵青,膝蓋也早已紅腫了,他一邊讓婢女替他上藥,一面喚來謀士張文冕商量對策。
張文冕道:“劉公的确得加快步伐了,萬歲這是等不及了。”
劉瑾沒好氣道:“不是你說這事兒不能操之過急嗎!”
張文冕不徐不急道:“若依常理,的确應徐徐圖之,以減少沖突。可萬歲年少氣盛,到底少了耐性與穩重。劉公為人臣下,也隻能盡言厲害,再由萬歲自己做主。”
劉瑾歎道:“是啊,我們這些狗奴才,也隻能指哪兒打哪兒了。”
七日之後,他就呈上了奏報,言說查明了戴珊案的真相,揭發是戶部侍郎陳清因與戴珊有仇,所以害其家兩個孫兒,并嫁禍給定國公府。而陳清正是反對設立東官廳的最激烈者之一。
月池得知這一消息,怒急反笑,直接摔了茶盞:“呸,從未見過如此心思詭詐之徒!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真真不要臉!”
可不論月池和少數人如何憤慨,東廠所造的僞證,至少目前看來是天衣無縫,有許多人因此也相信了,因為陳清和戴珊早年的确也因政見不合起過争執,兩人迄今見面也是皮笑肉不笑。
不少人一面看着陳清痛哭流涕、大喊冤枉,一面指指點點、竊竊私語:“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面上瞧着光風霁月,心裡卻是毒如蛇蠍。”
陳清數十年的官聲就此毀于一旦,全家人也跟着跌落泥沼之中。這勳貴因繼承權之争陷入内鬥,文官也削去一位侍郎及黨羽而實力削弱。李東陽何等眼明心亮,隻覺觸目驚心,他再三懇求朱厚照,到此為止,還陳清一個清白。
朱厚照卻不願收手,他一定要赢,而且要赢得她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