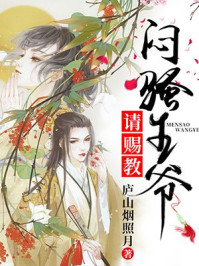朱厚照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月池茫然地坐在篝火前,這火是在幾十根粗木搭建的木台之上,紅彤彤的焰火比人還要高。一群皮膚雪白,鼻高眼深的回族美女正繞着篝火翩翩起舞,她們頭頂戴着深紅色的小帽,帽頂都插着一根雪白的羽毛。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她們的靈動的手指,柔軟的腰肢與輕巧的舞步,還有那疾轉時,如鮮花怒放一般盛開的裙擺。
朱厚照就坐在月池身旁,時不時用回語大聲叫好,有時甚至還能與那些大膽的姑娘們對話一兩句,一旁的回語通譯鼓起勇氣拍馬屁:“皇爺真是天縱奇才,小的花了兩年時間才勉強聽得懂她們說話,可萬歲隻用了一會兒,就無師自通了!”
可朱厚照明顯沒有聽他說話的興緻,他學梵語都隻用了兩三個月,就可以熟練地聽說讀寫天竺的佛教典籍,現在隻是說幾句話而已,又有什麼稀奇的。更何況,他手裡的鐵叉上還烤着鹿肉呢。鮮紅的鹿肉在烈火上慢慢變熟,滾燙的油脂在鐵叉上滴滴答答地落進火裡。朱厚照還知道翻個面,最後再随手撒上了一把孜然就遞給月池。
月池一驚,這才如夢初醒,她低頭一瞥就看到了鹿肉上的幾處焦黑:“……您還是自己吃吧。”
朱厚照第一次還沒反應過來:“你同朕客氣什麼?”
月池誠懇地望着他:“臣真不是客氣。”
朱厚照一愣,他的眉頭一皺:“你是嫌它不好吃?”
一旁的通譯是第一次進宮,連天顔都不敢怎麼直視,哪裡見過這等“不識擡舉”之人,他隻聽月池答道:“您可以先嘗嘗啊。”
通譯偷偷一看,皇爺居然真吃了一口,剛剛嚼了一兩下,眉頭就皺得更深了,他吓得魂不附體,還以為下一刻天王老子就要發怒。誰知朱厚照居然笑開,信誓旦旦道:“明明這麼好吃!你真是有眼不識金鑲玉。”
饒是心情郁郁的月池都被他逗笑了片刻:“是嗎,那切一塊給我好了。”
說着,她就拿起了小刀,朱厚照一驚,他忙側身躲開:“剛剛給你吃,你不要,現在朕覺得不錯,不舍得給你了。”
月池揶揄道:“那好吧,真是可惜呀,那您就自個兒享用完吧。”
這下可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朱厚照咬牙在月池的灼灼目光下硬咽下去了好幾口又腥又寡淡的鹿肉,最後實在受不了了。他瞥見了一旁的樂隊,忽然福至心靈,扭頭對月池道:“你還沒聽過朕奏樂吧,今天就讓你開開眼界。”
說着,他擡腳就向樂隊裡走去,一衆樂師立刻起身跪倒在地上。樂聲驟然停,舞女們也急急地轉過身來,琥珀色的大眼睛中滿是迷茫。朱厚照随意擺了擺手,正準備挑一樣樂器,誰知觸目所及都是筚篥、唢呐、手鼓、銅角、螺貝等回族的樂器,唯一一個眼熟一點的就是琵琶。他隻覺心頭一哽,這要怎麼彈,可就這麼回去未免太丢臉了。他下意識回頭去看月池,隻見她坐在火堆邊正望着這裡,溫暖的火光融進了她的眼波中,就像盛滿绮霞的澄江。
可在察覺到他目光以後,她卻立刻别過頭去,不再繼續看他。朱厚照隻覺心頭一空,他還是拿起了琵琶,擡手示意晚會繼續。月池驚詫看到一個個悅耳的音符從他的指尖中跳躍出來,柔和婉轉,悠揚動聽。是了,他從小就有極高的音樂天賦,隻是沒想到,除了歌唱得好,還能彈一首好琵琶。一旁的樂師也回過神來,一時筚篥渾厚,手鼓咚咚,舞女們也默契地一齊起舞,修長的玉臂在紅紗下若隐若現,纖細的手指亦如蓮花的瓣顫。
一曲終了,在場所有人都有心曠神怡之感,劉瑾等人更是擁上來,把一首琵琶小調誇得“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朱厚照卻興沖沖地看向月池:“怎麼樣,不錯吧。”
月池無奈地看着他,他們在一塊朝夕相對也快四年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她既欽佩他的天資聰穎,又厭惡他的辣手無情;既見憐他的天真童趣,又膩煩他的世故老練,一個人怎麼能集這麼多截然相反的特質于一身呢,朱厚照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她忍不住問了出來,朱厚照驚訝地看着她,他臉上有些發紅:“你怎麼突然想起這麼問了,你爹我當然是,文治武功冠絕古今的一代英主了!”
月池:“……”有時還很白癡,八成是腦子被什麼糊住了。
這一場歌舞升平,直到深夜方停歇。這時才起駕回乾清宮就太晚了,朱厚照當機立斷,今晚就歇在南台。南台位于太液池之南,是帝王閱稼之所,中有一大片水田村舍。在一排排琉璃宮燈的映照下,田間稻谷菜花,梁上的茅屋籬笆顯得是那麼的,不合時宜。月池腹诽道,不管是哪個年代的農家樂,都是忽悠人的居多。朱厚照卻很滿意,特别是見到屋内的紙窗、油燈、織機、木榻時,更覺新奇。
他在木床上打了滾,笑道:“朕還從來沒睡過這麼小的床。阿越,你以前在民間時,睡過這樣的的床嗎?”
月池望了床上的繡帳錦被一眼:“沒有。”
朱厚照起身道:“難不成你以前睡得床比這還小?”
我以前睡得是兩米的席夢思!月池打了個哈切:“稍微小上一點。萬歲,太晚了,臣還是先告退了。”
“等等!”朱厚照果不其然又一次叫住了她。月池回頭道:“這床睡不下兩個人。”
朱厚照下意識看向地上,月池忙道:“我也不想打地鋪。”
“那你就……”朱厚照又看向了羅漢床,月池道,“臣的名聲已經很差了,您就不要再火上澆油了。”
朱厚照失笑:“不招人妒是庸才,和朕有什麼關系。你今晚睡在這裡,名聲也不會更臭,離開這裡,名聲也不會好轉。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從心而為呢?朕還想問問你,今兒到底是怎麼了?”
最後一句戳中了月池的心病,她躺在了屏風後面,如水的月光透過紙窗傾洩而下,照得屋内如積水空明。朱厚照側身看着她隐隐綽綽的身影問道:“是張岐給你小鞋穿了?”
月池輕聲道:“不是。”
朱厚照又問:“那是其他人說閑話了?”
月池搖搖頭:“流言蜚語,不足為懼。”
朱厚照心道果然:“是戴珊,他說了什麼?”
月池一愣,她幽幽道:“也不是他。臣隻是,想到了一個故事。”
她的眼前陡然浮現了那些傷痕累累、皿迹斑斑,她低聲道:“從前有個烏有國,烏有國的國王很厭惡山林中的野獸,于是重金懸賞,要制成一件舉世無雙的皮草衣裳。獵人們因此在山間四處捕獵。有一天,有一群小狐狸,誤入了獵人的陷阱。它們被捕獸夾夾住了腿,腿上皿肉模糊,它們不住地哭泣求饒,可并沒有換來獵人絲毫的憐憫。它們的親人也在遠處哀鳴,卻不敢靠近,隻能眼睜睜看着它們,被扒掉了皮,做成了狐皮大髦……為了達成目的,而害了弱小的性命,您覺得,這麼做對嗎?”
朱厚照的聲音透過屏風傳來,仿佛摻了冰渣子:“那你在問這個問題之前,為何不想想,烏有國的國王為什麼會厭惡野獸?”
月池道:“猛獸吃人,自然當為民除害,可幼狐無辜,卻隻是被牽連。它們應該得到一個公道。”
朱厚照霍然起身道:“朕已經足夠仁慈了。你還要朕把狐狸擡進太廟裡來供着嗎?”
月池深吸一口氣:“臣不敢。”
朱厚照見她如此,也不由軟了幾分,可說出的話卻直插心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狐狸雖是野狐,也是烏有國王的畜生。為國王增光添彩,是它們的榮耀,也無法逃避的義務。它們不該心生怨怼,而該為族群而羞愧自省,并為國王的仁慈心存感恩。”
月池久久地沒有言語,朱厚照不由問她:“你在想什麼?”
月池道:“我在想我的皮,适合給您做一件什麼。”
朱厚照失笑,他翻了個身:“放心吧,朕暫時還是覺得,你的皮毛還是長在你自個兒身上比較好看。不過你說得,倒也讓朕動了恻隐之心,都察院監裡沒什麼大錯的,申斥幾句後,近日就趕快放出來吧。”
寒意順着月華一點點的滲透到她的肌理裡,月池忍不住擁了擁被子,這既是告誡,又是警告。他不希望她插手進去,反而要她盡快息事甯人。如果不聽他的話,戴家就是她的前車之鑒,可如果聽了他的話,又教她于心何忍。
她躺在羅漢床上一夜難眠,直到天明時才微微睡了一會兒,再一次醒來時,一睜眼就看到了朱厚照的大臉靠在她的枕邊。
月池吓得尖叫,一把就把他掀開。朱厚照被推得坐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月池先發制人:“您這是做什麼!”
朱厚照也是一臉理直氣壯:“朕隻是想叫你起床看猴戲而已,你這麼大反應做什麼?”
月池一愣:“看什麼?”晚上看歌舞,早上看猴戲,你成日這麼會玩,太廟裡的老狐狸們知道嗎?